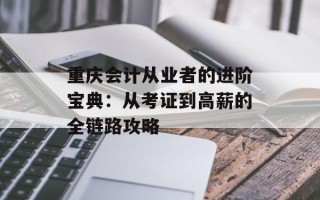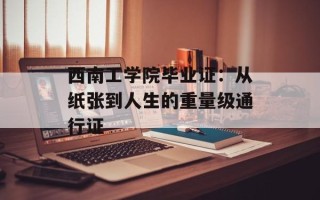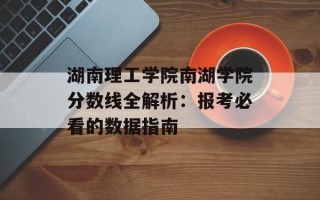不应对中国疫苗失去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高福力挺中国疫苗 摄影/本报记者 蒋若静
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发现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GMP)的行为,疫苗安全问题引发全国热议。在昨天上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力挺中国疫苗:中国生物制品、疫苗研发位居全球先进之列,不应对中国疫苗失去信心。同时,他还对狂犬病的消除问题提出见解,认为应该给狗打狂犬疫苗,从源头上遏制狂犬病的传播。
谈疫苗安全
疫苗不等于“疫苗问题”
应与产销环节区分开
高福说,中国疫苗出现的问题,每一个都是具体问题,但一定要把“疫苗”和“疫苗问题”区分开。“我作为疾控中心主任,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中国疫苗,很好!”高福提醒,应该将疫苗本身与疫苗生产、销售等环节区分开。
据高福介绍,中国的生物制品、疫苗研发不比发达国家差,在全世界更佳之列。中国一些疫苗经过世卫组织认证,已经向世界推广,比如中国乙型脑炎疫苗已经在一些国家使用。针对疫苗领域出现的问题,高福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不要对中国的疫苗失去信心。
谈SARS病毒
新发传染病是世界性挑战
但SARS事件不会再有
“SARS(非典)已经过去十几年了,还会再来吗?”面对这个问题,高福说,SARS来不来,SARS的“兄弟姐妹”来不来,我们管不了,因为新发、突发传染病是世界性挑战。“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事件’不会有了,这得益于我国传染病监测 *** 建设得很好,病毒来了我们可以挡住它。”
高福举了一个典型案例,曾经有一位韩国携带莫斯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患者进入中国,我们对其进行及时隔离和治疗,使得莫斯病毒没有在中国传播。而莫斯病毒在韩国传染了186位病人,导致39个死亡病例。
“SARS这样的病毒随时可能有,但是SARS事件不会再有。”高福说。
谈狂犬病
建议给狗普遍打疫苗
从源头上消除狂犬病
去年的长生事件涉及到狂犬疫苗,也让人们不禁关注到了狂犬病的控制问题。狂犬病是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人畜共患传染病,临床表现为特有的恐水、怕风、咽肌痉挛、进行性瘫痪等。由于目前对于狂犬病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人和动物患狂犬病后的病死率几近100%。近年来,患狂犬病死亡人数一直排在我国法定传染病死亡人数的前列。
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消除狂犬病?高福建议,要给狗打狂犬病疫苗,从源头上遏制狂犬病的传播,因为这个是人畜共患病。高福进一步解释:“一定要注意,不是不给人打,现在在中国被狗咬了还是要打狂犬疫苗。未来,如果给狗普遍打疫苗了,就意味着狗身上没有狂犬病毒了。如果全中国的狗没有狂犬病了,被狗咬一下也就没事了。世界上一些国家消灭狂犬病,靠的就是把狂犬疫苗打给狗。”
对于狂犬病的消除问题,高福进一步解释,他通过在基层调研之后发现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流浪狗没有人管。“我建议要落实到基层,呼吁基层来管。比如,城市里要社区来管理,农村则要村长管、镇长管,要做到职责到人,作为基层领导的职责之一。”
高福说,全国各地的基层疾控系统不断紧抓重视狂犬病问题,去年狂犬病致死案例只有400多例,而本世纪前十年间,有时候一年多达2000例至3000例。相比之下,现在已经控制得好很多了。
相关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研究员岳秉飞
提高犬只疫苗接种覆盖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研究员岳秉飞也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狂犬病的控制。他引用了更加详细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犬用狂犬疫苗采购量约三千万头份左右,而养犬数量在八千万到一亿三千万之间波动,免疫接种比例在三分之一左右,防疫风险较大。另外,我国人用狂犬疫苗2017年批签发上市892批次,1702.7万头份,可以说接种量非常大。
岳秉飞说,在发达国家,人被犬咬伤之后,医生会先询问咬人犬的健康情况,如果犬没有表现异常且打过狂犬病疫苗,人大多就不需要打针。像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犬都是普遍接受狂犬病强制免疫的。
我国的狂犬病预防主要集中在“咬伤后治疗”环节,往往是人类被犬类咬伤后,人类再接种狂犬疫苗。被咬了再补救,本末倒置,造成巨大的浪费。一些成功消除家养动物传播狂犬病的发达国家经验显示,如果彻底控制传染源,就能很轻易地解决狂犬病的问题。
对此,岳秉飞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狂犬病毒的宿主是犬类动物,控制狂犬病的流行必须从源头抓起,大力加强犬只免疫管理,提高接种覆盖率。具体措施包括,强化养犬的登记注册,建立档案,明确定期免疫接种疫苗,发放免疫登记卡并加施免疫电子标识。有免疫标识的犬即使出现咬人情况也不必接种狂犬疫苗。同时还要加大对养犬人进行法制教育,明确养犬人的法律责任,加强公共安全意识,定期接种疫苗。同时,强化责任意识,减少遗弃。
本组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高福终于把美国防疫中的这个“大错误”给指出来了中国疾控中心高福院士,近日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的防疫措施,尤其是中国有哪些应对经验值得被借鉴,欧美国家都犯下了哪些错误等等。
高福则在采访中明确地点出了欧美国家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在我看来,欧美犯下的一个大错误,是人们没有戴口罩”,高福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道。
(截图来自《科学》杂志的报道)
《科学》杂志对他的专访文章也表示:“中国顶尖的科学家说:在应对新冠病毒时不戴口罩进行保护是‘大错误’”。
高福还进一步表示:新冠病毒是通过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的,其中飞沫在传播中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人们必须要戴口罩,因为说话的时候就肯定会有飞沫从嘴里喷出来。
“很多无症状和潜伏期的感染者,如果他们戴上口罩,就可以防止携带患者的飞沫抛出来并传染给其他人”,他说。
(截图来自《科学》杂志的报道)
这段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成为“真理”,但对欧美国家的来说还“满不在乎”的信息,也被采访高福的《科学》杂志记者Jon Cohen发到了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
根据这位记者的介绍,美国食药监局的前专员Scott Gottlieb近日也曾呼吁应强制全民都在出门时佩戴口罩,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就将很难再通过呼吸道的飞沫将病毒传染出去了,而如今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高福在采访中也做出了类似的观点。
“但Scott Gottlieb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美国缺乏(口罩)供应,人们现在将会从医疗人员那里拿走它们(口罩)。所以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去提高产能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2月初,耿直哥曾经采访过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全球卫生研究所的教授和行政总监罗伯特·墨菲(Robert L. Murphy),当时他的观点却和高福以及Sott Gottlieb的完全相反,认为口罩根本无法阻挡新冠病毒,只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连N95级别的口罩,其防护性也是有限的。他还表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佩戴这些口罩可以保护人不受呼吸系统病毒的传染。
但同为美国人的Scott Gottlieb却在一段采访视频中表示,他认为如果所有人出门都能戴口罩,是可以大大降低无症状感染者通过飞沫病毒传播给他人的风险的,而且对于流感的研究也证实了口罩其实可以降低5成左右的传染风险。
可惜的是,在目前美国感染人数已经突破10万的情况下,现在才去意识到口罩的重要性,可能有些晚了……?
最后,除了口罩的问题,高福还在《科学》杂志的专访中分享了其他中国抗疫方面的经验,包括应禁止人群聚集,限制出行,与他人保持距离;必须隔离所有感染者;密切接触者也必须被隔离等等。高福还尤其强调轻症患者必须被隔离,而且这个措施也应该被世界其他地方所采用,因为这样才能控制住传播的源头。
高福还表示中国在户外众多场所进行的大规模体温测量也值得借鉴,因为这样可以及时让高温的人离开人群。
在被问到为何中国1月20日才知道病毒可以人传人,之前为什么观测不到时,高福表示当时并没有详细的流行病学数据,而且科学家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种极为疯狂和很善于隐藏的病毒,所以不仅是中国,欧洲和美国一开始都低估了,以为这只是一种普通的病毒。
而在被问到病毒到底源自哪里,是不是11月就出现在武汉时,高福则表示科学家正在努力搞清楚病毒的来源,但如今看来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并不一定是最初每个人都以为的源头了,也有可能只是疫情出现加剧的一个地方。不过,他也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病毒早在11月就出现在武汉了。
至于如何看待美国政客“武汉病毒”一说,高福的回答是“称病毒为中国病毒肯定是不对的,这个病毒来自地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截图来自《科学》杂志的报道)
另外,高福还表示中国目前并没有实现对新冠病毒所谓的“群体免疫”,现在的策略就是尽量给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争取时间。
(截图来自《科学》杂志的报道)
来源:环球时报新媒体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转移病房不能算“已出现超级传播者”【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转移病房不能算“已出现超级传播者”】针对有媒体报道“已出现超级传播者”的说法,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应称:发生在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1名患者传染14名医务人员”事件,不能算“已出现超级传播者”。
记者了解到,25日有报道提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一名患者总共转了4次病房,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北京大学的一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位感染多位医务人员的患者可以被认定为‘超级传播者’。”
高福表示,由于该患者多次转移病房,所以不能算是“超级传播者”。“所以在卫生应急状态下,大家不要慌,优秀到位的管理非常重要。”
记者求证其他多位权威疾控专家,均认同高福对此的判断。
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说,还没有证据说已经有了“超级传播者”。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们当务之急是以科学思维开展防控治。”高福表示。
责编:郭姝婷
中疾控主任高福藉《科学》发声,解释早期为何难定“人传人”新冠病毒是否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
中国分享病毒数据是否及时?
为何中国流行病学家早期难以看出人传人的证据?
高福对此做出回应
- 资料图:高福。近日,在接受美国《科学(Science)》采访时,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应了前述种种争议,并指出“美国和欧洲防控过程中,更大的错误是人们没有戴口罩”。
新冠病毒是否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中国分享病毒数据是否及时?为何中国流行病学家早期难以看出“人传人”?近日,在接受美国《科学(Science)》采访时,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应了前述种种争议,并指出“美国和欧洲防控过程中,更大的错误是人们没有戴口罩”。
(截图来自《科学》杂志的报道)
高福还进一步表示:新冠病毒是通过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的,其中飞沫在传播中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人们必须要戴口罩,因为说话的时候就肯定会有飞沫从嘴里喷出来。
“很多无症状和潜伏期的感染者,如果他们戴上口罩,就可以防止携带患者的飞沫抛出来并传染给其他人”,他说。
(截图来自《科学》杂志的报道)
这段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成为“真理”,但对欧美国家的来说还“满不在乎”的信息,也被采访高福的《科学》杂志记者Jon Cohen发到了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
59岁的高福专长于研究包膜病毒,它们如何进入细胞以及在物种之间移动,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本科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后在牛津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专门研究免疫学和病毒学。
新冠疫情暴发后,高福和他所在中国疾控中心曾深陷舆论漩涡。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网站上发表回溯性研究,展示了425名感染者流行病学情况,因数据与官方通报多项不一致,中国疾控中心一度遭受“人传人知情而不报”的指责。论文风波后,高福鲜少在国内媒体上直接露面。此次采访,《科学》动用短信、语音邮件和 *** 等多种渠道沟通,并于3月27日刊登。
在被问到为何中国1月20日才知道病毒可以人传人,之前为什么观测不到时,高福表示当时并没有详细的流行病学数据,而且科学家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种极为疯狂和很善于隐藏的病毒,所以不仅是中国,欧洲和美国一开始都低估了,以为这只是一种普通的病毒。
(截图来自《科学》杂志的报道)
(Q:It wasn’t until 20 January that Chinese scientists officially said there was clear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 *** ission. Why do you think epidemiologists in China had so much difficulty seeing that it was occurring?
A:Detailed epidemiological data were not available yet. And we were facing a very crazy and concealed viru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same is true in Italy, elsewher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cientists, everybody thought:“Well, it’s just a virus.”)
2020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首次分离,确定该病毒是引起武汉出现的肺炎疫情的病原体。而这一进展最早并非由中国科学家披露。1月8日,《华尔街日报》发布一则消息,中国研究者发现新的冠状病毒。几小时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接受新华社采访证实这一发现,并称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也已在1月7日获得。
为什么不是中国科学家率先报道新冠状病毒的出现?“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一个很好的猜测”,高福未正面回复,只是称,《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与官方分享病毒信息只有几个小时差,不超过一天。
(Q:China was also criticized for not sharing the viral sequence immediately. The story about a new coronavirus came out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n 8 January;it didn’t come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scientists. Why not?
A:That was a very good guess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HO was informed about the sequence, and I think the time between the article appearing and the official sharing of the sequence was maybe a few hours. I don’t think it’s more than a day.)
1月9日,在《科学》官网的一篇报道中,多位科学家呼吁,希望尽快获知更多有关此次肺炎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的信息、查明确切动物感染源。1月11日上午,悉尼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霍尔姆斯(Edward Holmes)代表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 教授张永振在virologic.org上披露新冠病毒的“初始”序列。这一序列最早测出的时间是1月5日,并立即上报,同时上传至NCBI GenBank数据库,为保证准确,后续还进行过修正。该数据库是由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建立并维护的公共综合性序列数据库,研究者可以从中查找已知的基因序列进行分析。
1月11日当晚,国家卫健委宣布中国将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第二天,另外5个来自不同患者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由国家卫健委领导小组在全球共享流感病毒数据库GISAID发布,序列来自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医科院、中国疾控中心。
世卫组织在1月12日的声明中表示收到基因序列,“对正在进行的调查的质量和在武汉实施的应对措施以及定期共享信息的承诺感到放心。”
目前,全球公开的新冠病毒序列大约有200个。
对于早期病毒数据公布不及时的质疑,高福予以否认,并表示“我们已经及时与科学同行共享信息,但这涉及公共卫生,我们必须等待政策制定者公开宣布”。他提到,不希望引起恐慌,当时没有人能预言这种病毒会引起大流行。
谈及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是否为病毒最初来源,高福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即市场可能是最初起源,也可能是病毒扩散开来的地方。他表示,正在努力了解病毒起源,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11月出现了疫情”。医学期刊《柳叶刀》1月曾发文披露金银潭医院收治的前41例病例情况,研究图表显示,前四名感染者中有三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这为一直被认为是疫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打上问号。
此外,高福分享了中国研究领域的进展:中国正在将猴子和转基因小鼠动物模型应用于测试评估药物和疫苗,研究显示“猴子模型有效”;治疗药物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数据将在4月出来。
目前,海外新冠疫情仍呈暴发态势。基于前期防控的经验,高福提醒,远离社交是控制任何传染病(尤其是呼吸道感染)的基本策略。
首先,使用“非药物策略”,没有任何特定的抑制剂或药物,也没有任何疫苗;
其次,必须确保隔离所有病例;
第三,密切接触者必须隔离,中国花费大量时间找到所有密切接触者,并确保隔离;
第四,暂停公共聚会;
第五,限制交通。
高福:中国疫苗一直处在世界“之一梯队”冠状病毒作为大流行病早有预兆央广网北京11月12日消息(记者 马可佳)第五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11月12日开幕。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博览会的医疗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做“新冠大流行与医药产业发展”主题的演讲。回顾新冠肺炎全球蔓延的整个过程,高福认为,中国的疫苗(研发)一直处于之一方阵,之一梯队。中国以科学、求真的态度赢得了应对疫情的时间。
谈到中国的防控经验,高福认为,中国对新冠疫情防控的贡献在全球公共卫生界可以写进教科书。中国用了一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测序,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对病毒进行了分离。2020年的1月10日,中国把病毒的基因组序列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分享。
此外,中国疾控中心还呼吁全球戴口罩应对新冠疫情。“2020年1月26日白岩松采访我,我就代表团队向全国人民呼吁戴口罩,倡导口罩文化。3月27日我在美国的《科学》杂志呼吁全球戴口罩。”
高福将新冠疫情的出现归结为“灰犀牛事件”。据国际大流行应对委员会研究推演发现,冠状病毒作为大流行病早有预兆。1965年开始,已经发现7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包括1965年发现的病毒HCoV-229E;1967年发现的病毒HCoV-OC43;1995年发现的病毒HCoV-HKUI;2002年发现的SARS病毒;2004年发现的病毒HCoV-NL63;2012年发现的MERS;2021年发现的COVID-19等。
而中国在疫苗的研究、研发方面一直处于世界之一方阵、之一梯队。中国已有7款国产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或开展紧急使用,其中包括5款灭活疫苗(国药、科兴等),1款腺病毒载体疫苗(康希诺),1款重组蛋白疫苗。
高福说,人类不断地研发疫苗,病毒也在不断地变异,这是人类和病毒的博弈。现有数据表明,虽然在防感染、防发病、防传播方面效率有所下降,疫苗提供的基础免疫对预防重症和死亡、减轻疾病负担的效果仍然非常好。
与西方一些国家不同。中国从起始阶段控制疫情到现在一直坚持“清零”政策,高福表示“正是‘清零’政策给我们抢出了时间,让我们去进一步认知新冠病毒,让我们去把物资准备好,让我们把疫苗研发好,让我们把疫苗打下去,让我们有了相关的药物,我们的医疗设施也准备好了。‘清零’政策给中国赢得了时间。”
中国对疫情有效控制的程度,高福认为,如同国际上发生的是海啸,中国发生的是海浪。面对新冠疫情,首先要向科学要答案,以科学为基础;其次需要公众的理解,例如积极佩戴口罩;最后就是强有力的行政决策,制度优势和民众的集体智慧帮助做这样的决策,从而使中国新冠疫情的防控走在了世界前列。
在预防新冠疫情的同时,高福也提到,全球都应该警惕“信息流行病”,也可以看成一种"信息病毒"。就是网上经常会有一些让大家搞不明白的信息,真假信息混合在一起。从疫情出现开始,网上也在流行“信息病毒”。比如有人说打疫苗不好,不要打第三针疫苗之类的。高福表示,”打疫苗是个收益与风险平衡的问题。如果没有新冠,我们也不号召大家去打疫苗。但是有了新冠了,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我们打了疫苗的风险相比,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
此外,高福还在发言时呼吁希望提高对mRNA(即Messenger RNA 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关注。他表示,除疫苗外,遗传病、罕见病、肿瘤以及各种代谢病的许多问题都可能通过mRNA技术来解决。希望投资者关注对mRNA技术的投资。“我们不共享疫苗,病毒将共享世界”。
独家专访高福,新冠疫苗研发如何摆脱“卡脑子”问题?2021年7月9日,高福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张岩 / 摄)
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认为,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目前走在世界之一方阵、之一梯队。
|作者:隋坤
2021年7月8日晚11点半,当记者联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时,他仍在与同事、学生们开研讨会,主题是关于新冠病毒的变异株。
第二天中午,记者终于在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见到了刚刚散会的高福,他的脸上略有一丝疲惫。在采访现场,高福让记者把夹在他腰带上的话筒藏进衬衣里,并开玩笑道:“既然做一件事(拍视频),就尽量做到更好。”
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这位院士曾因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公开透明疫情信息而被 *** 攻击。而作为参与了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的科学家,高福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疫苗与病毒赛跑,以及如何让全球疫苗研发不再“卡脑子”。对于中国疫苗,他坚定地说:“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
“没有疫苗出现,
就很难想象免疫学的发展”
谈及疫苗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高福连用了两个“非常”:“疫苗在疾控史上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还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
在疫苗技术尚不成熟时,人类历史进程多次受到瘟疫的重大影响。
14世纪,鼠疫杆菌引起的黑死病让欧洲人口锐减,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一书里提到英国的死亡人数:英国从1348年开始大规模暴发黑死病,经过100年时间,人口从600万减少到了200万,整整减少了2/3。
·中世纪欧洲画家描绘黑死病的作品《死亡的胜利》。
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病毒的人数高达1.5亿。从17世纪到18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英国女王玛丽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等多国君王都病亡于天花病毒。
直到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一个意外发现,让人类逐渐打开了疫苗与免疫学的大门。
18世纪下半叶,詹纳发现天花疫区的很多挤奶工面容光洁,几乎没有天花发病留下的疤痕。这让他想起了当地的一个传言,“得过牛痘的人便不会再患天花”。1796 年,詹纳在8岁的小男孩詹姆斯·菲普斯身上接种了牛痘病毒。大约6周后,詹纳又为痊愈的菲普斯接种了天花病毒,结果菲普斯没有感染天花。后来,詹纳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菲普斯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并非孤例。天花疫苗就此诞生。
这是疫苗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虽然詹纳不是之一个尝试接种牛痘以预防天花的人,但他之一次基于实验数据作出公开、科学的论述,奠定了疫苗的理论基础。高福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没有疫苗出现,就很难想象免疫学的发展。”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病毒。
·建于1867年的天津保赤堂牛痘局,免费为儿童施种牛痘天花疫苗。
之后,疫苗研发技术快速发展。高福说:“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某类微生物所引起的疾病从地球上彻底消灭,人类用疫苗做到了,比如天花和牛瘟。通过疫苗,我们还在区域内消除了脊髓灰质炎,乙肝的发病率也从1/10降低到了3‰,狂犬病疫苗则将无数人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
通过接种疫苗,我国麻疹、百日咳、流脑、乙脑、甲肝等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更低水平。其中,2012年的麻疹发病率较1978年下降了99.7%。“1978年,中国开始了‘免疫规划’,孩子一出生就打各种疫苗。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这么快(2020年已达77.3岁),疫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至今没有任何一种医疗措施能像疫苗一样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如此重要、持久和深远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一种治疗药品能像疫苗一样以极其低廉的代价让某一种疾病从地球上被“消灭”。中国科学院院士、免疫学专家董晨曾说:“疫苗是我们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发现的保护我们机体的重要手段。”
但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上,疫苗仍非“常胜将军”。高福说:“目前还有疫苗无法战胜的疾病。比如面对艾滋病毒,人类一直没有研制出有效疫苗。目前人类面对很多病毒仍然知之甚少,背后的很多科学机制都没有弄清楚,迄今也没有疫苗,我们需要就这些问题向科学要答案。”
争分夺秒,
把P3实验室直接转换成生产车间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疫苗可能是最终解决问题的答案。高福说:“从一发现病毒,我们就知道疫苗在防控传染的巨大作用,也是最终解决方案。”
2020年2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的一次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取得阶段性进展”。彼时,有关部门在疫苗技术上布局了多条路线,其中走得最快的正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灭活疫苗。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谈及中国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发,高福热情地向记者推荐了一位特殊的采访对象——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
2020年1月初,武桂珍和团队拿到了新冠病毒标本。随后他们凭借强大的科研实力率先完成了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找出了病原,并共享给全球科学家。“正是基于此基因序列,世界各国科学家才创纪录地研制出上百种疫苗。”高福说。
·2021年7月9日,武桂珍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张岩 / 摄)

仅过了几天,武桂珍与团队将新冠病毒分离培养成功,并制备出疫苗株。这是灭活疫苗研发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在毒株分离过程中要保证绝对的生物安全,必须在P3实验室进行。P3实验室全名为“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属于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为防病毒泄漏,P3实验室内部通常是负压环境,且装置了具有高效过滤器的排风装置。在P3实验室内,工作人员需着防护服,经由缓冲间到达核心区域,每人连续工作不能超过4个小时。
P3实验室的工作环境会让人体不舒服。“进入实验室之前要经过多重检测,甚至连工作人员心理状态也要考虑到。如果某人前一天被不愉快的事影响了心情,我们会建议他不要进入实验室。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们则会不允许他进入实验室。”武桂珍说。
毒株分离培养成功之后,中国初步具备了研发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基础。经过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一系列科研攻坚,中国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很快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也意味着需要对接企业、提高产量。“当时还没有适合专门生产新冠病毒疫苗的车间,只能由P3实验室转换。”此时,武桂珍面临着“几乎不可承受”的压力:“普通P3实验室病毒培养量有一定限制,但转换成生产车间后,我们实验室将接触比此前多几十万倍的病毒培养量。病毒培养量越多,病毒泄漏的风险就越大。”
关键时刻,疫苗的研发生产不能等。高福、武桂珍顶住压力,选择了“发酵罐”生产方式。“与其他方式相比,这是一种相对更安全的生产方式,因为它是全封闭的。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放心。后期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最终证明了这种生产 *** 的高安全性。2020年4月27日,经专家认证及卫健委同意,我们将P3实验室转换成了生产车间,并开始了灭活疫苗的一期与二期临床试验。”
从疫苗的研发到生产,是一个与病毒赛跑的过程,高福对此深有感触:“武桂珍的担当为中国疫苗的研制抢了足足三四个月的时间,这是我们中国新冠病毒疫苗走在世界之一方阵之一梯队的关键因素。”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布局了5条技术路线,除了灭活疫苗,还有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高福带领研发的是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新冠病毒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他带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团队,开始设计针对β冠状病毒感染性疾病的通用疫苗构建策略。这种疫苗是通过基因工程 *** ,在体外制备病毒的S蛋白受体结合区域(RBD)二聚体, *** 人体产生抗体。高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重组蛋白苗的技术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大家耳熟能详的乙肝疫苗就属于此类疫苗。”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院士团队合作企业研发的重组蛋白亚单位新冠病毒疫苗。
2020年11月,高福研制的疫苗陆续在国内及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厄瓜多尔等国启动三期临床试验,进展顺利。特别是得到了首个试验启动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高度认可,在该国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成为国际上之一个获批临床使用的新冠病毒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2021年3月,该疫苗在国内获准紧急使用,接种者需要需要间隔一个月和六个月接种三针。
与其他科研人员一样,高福在疫苗研发的过程中同样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但也有些压力是特殊的,比如,新冠病毒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获准使用的时间点比其他疫苗稍晚。面对记者,高福正面回应了这种压力:“做科学的人,压力常伴左右,承受不住压力的人不适合搞科学。包括疫苗在内的科学研究,目的是创造、创新,无论时间早晚,我们都要力争走在世界的前沿。”
按照以往惯例,一款疫苗从研发到批量生产需要8到10年时间。但此次中国在短时间内就研制成功了若干种类疫苗,背后原因是什么?当记者问起这个问题,高福和武桂珍都提到了一个词——制度优势。“有国家作后盾,我们敢担当,敢拍板。在统一指挥下,我们的审批流程被缩短,各方力量的配合更加紧密、高效。”武桂珍说。此外,高福还提到了“科学基础的积累”:“中国这么多年来对科技的投入、对疫苗的投入,都使我们积累了良好的科学基础,而良好的科学基础又加快了行政决策的效率。”
两位专家还谈到了中国疫苗的安全性问题。武桂珍说:“我们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但相关的所有程序都没有省掉。我们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比如动物实验、一期、二期、三期临床实验等等。就拿我们的灭活疫苗来说,其实安全性与有效性是非常高的。”
而高福则是一个行动派:“我早在去年5月就已经注射了国产疫苗,是之一批‘吃螃蟹的人’。”到今天为止我一共打了三针,疫苗种类与厂家都不尽相同,但身体没有任何不适。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对国家的疫苗有信心。如何判断好疫苗?安全、有效、可控、可及(经济上大多数人可获得),而中国疫苗做到了这4个方面。”
与病毒赛跑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是‘黑天鹅事件’,而是‘灰犀牛事件’。”在一次演讲中,高福如此说道。“黑天鹅事件”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而“灰犀牛事件”与之相反,指的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不易被关注的潜在危机。
高福说:“加上SARS与新冠病毒,人类已经发现了7种冠状病毒。2019年10月18日,盖茨基金会、世界银行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纽约做了一个桌面推演,叫作‘201事件’。推演中他们搞了个假想敌CAPS,翻译成汉语就叫作冠状病毒相关的肺炎综合征。”
类似推演的不止一个国际组织。高福是国际大流行监测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每年要开两次大会,探讨全球可能出现的大流行。“2019年大会的年度报告上就写着‘人类可能会遭遇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侵袭,新发突发病毒可能引发新的大流行’。”当时,大会将可能流行的病毒做了排名,其中排名第二的就是冠状病毒,鼠疫与埃博拉病毒都排在冠状病毒之后。
·2021年5月30日,高福院士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上作报告。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类之一次针对此类病毒研制疫苗。面对这个未知的敌人,科学家们面临的挑战有很多。高福说:“新冠病毒一直在适应人类,一直在变。病毒跟人类的关系就像是猫鼠游戏。”
“我们一直在测试,现有疫苗对越来越多的病毒变异株管用不管用。许多科学家都在与病毒赛跑,一方面他们做好监测,另一方面也在继续研发。”高福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道。“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研制更高效的疫苗,摆脱‘卡脑子’的问题,尽力突破人类的认知。我们要给科学时间,向科学要答案。”
幸运的是,高福与武桂珍都认为,目前中国疫苗对于人们最担心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依然有效。“大家经常问,现在这么多新变异株有什么影响?其实每次新的疫情发生,我们都会迅速作出诊断,同时进行毒株分离,然后做交叉综合实验,最后利用实验结果来观察疫苗的有效性。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疫苗都是管用的,尤其是面对关注度更高的德尔塔变异株。”
人们还关心疫苗有效期的问题。高福回答说:“这是人类之一次研制冠状病毒疫苗,很多东西是未知的,所以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高福表示,不排除新冠病毒未来像流感一样形成与人类长期共存的局面,所以“新冠病毒疫苗的发展方向也有可能会向流感疫苗靠拢”。据高福预测,未来社会将迎来“缓疫”状态,大家将会在满足一定防疫条件下进入正常生活。
正因如此,高福很重视即将召开的中俄后疫情时代传染病防控合作高峰论坛,以及冠状病毒国际前沿研究与创新论坛。他说:“全球防疫是一盘棋,世界如果不共享疫苗,病毒就将共享世界。”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正接待世卫组织专家据科学网,针对2月15日“贵州综合广播”等 *** 上散布的不实消息,《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资料图 新华社供图
高福表示,他现在正接待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世卫组织专家,研讨、沟通新冠肺炎的防治工作。
高福表示,在近日与世卫组织专家的科技与创新 *** 会议上,世卫组织对中国此次战“疫”工作和成效给予了很大肯定。他表示,中国一直坚持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原则和态度,和国际社会广泛合作。
据悉,高福领导下的中国疾控中心连日来一直联合全国疾控中心的驰援团在湖北一线开展病人的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中心也正在抓紧疫苗研发、药物测试工作,各种防控方案制定和科普宣传工作等也一直在有序进行中。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月14日宣布,协助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国际专家组所有成员预计本周末抵达中国。
正在刚果(金)访问的谭德塞当天在线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谭德塞说,世卫组织牵头的国际专家组与中方专家的合作进展顺利,国际专家组所有成员预计本周末抵达中国。
高福简历
高福,男,汉族,1961年出生,山西应县人。研究员,哲学博士。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
1983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1986年北京农业大学获硕士学位,1995年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至2004年任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2004年至2008年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2004年3月至今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0年至今任牛津大学客座教授。2008年至今担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2011年5月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201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院长,2017年7月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在包括Nature, Science, Cell, Lance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490余篇。任国际抗病毒联盟(ICAV)执委会委员;任《科学通报》杂志主编;共同创办Protein & Cell。任亚洲生物技术联盟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曾获(日本)日经(Nikki)亚洲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等。
来源:综合科学网 央视新闻 百度百科
编辑:tf10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转移病房不能算“已出现超级传播者”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王秉阳、屈婷)针对有媒体报道“已出现超级传播者”的说法,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应称:发生在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1名患者传染14名医务人员”事件,不能算“已出现超级传播者”。
记者了解到,25日有报道提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一名患者总共转了4次病房,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北京大学的一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位感染多位医务人员的患者可以被认定为‘超级传播者’。”
高福表示,由于该患者多次转移病房,所以不能算是“超级传播者”。“所以在卫生应急状态下,大家不要慌,优秀到位的管理非常重要。”
记者求证其他多位权威疾控专家,均认同高福对此的判断。
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说,还没有证据说已经有了“超级传播者”。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们当务之急是以科学思维开展防控治。”高福表示。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以争议论文为据,为被“群殴”的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正名!#高福#前言
近段时间疫情的严峻形势,导致国民狂躁不安,压力无处宣泄。但却因一篇被自媒体曲解的论文引爆全网,发展为大家对疾控中心高福主任的声讨,其实大家这样的压力状态,实质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也切不可因个人情绪而去伤害一个鞠躬尽瘁的科学家的心。每当我看到网上大家对高福主任恶语相向的时候,我总是愤慨不已,故而萌生了将这篇富有争议的英文论文翻译成中文,各中对错让大家自己细细品味,而不是听信自媒体的断章取义,捕风捉影。
根据此篇论文,我对 *** 谣言的回击
1. 中疾控科学家只写论文不抗疫?
如果大家细细的通读这篇论文,你会发现许多熟悉的名词,比如潜伏期,疑似病例,确诊病例,传播途径,实验室诊断标准等。那么这些数据从何而来呢?当然是来源于中疾控的数据研究,正是有了中疾控这篇论文研究成果的支持,才有了全国诊疗方案,流行病学调查方案,消毒防护方案,实验室诊断方案的出台。如果没有这些纲领性方案的出台,全国抗疫将如无头苍蝇,乱作一团。有了这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我们才能有方向,有目的,有条不紊的与疫情决战到底!
2. 网上嘲笑高福主任说过“儿童不易感,症状较轻”?
在大家通读这篇论文后,你会发现根据前期425例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确实发现感染者多为老年人,儿童不易感,症状多轻微。科学家以数据说话,不会主观臆断,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有数据支持。而且论文中写的非常清楚,会随着疫情进展,实时监测人群流行病学特征,进而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3. 网上抨击高福主任说过“不会人传人”?
针对这一抨击,明眼人都看出来这是某些自媒体为了人血流量的肆意栽赃!试问对于一个未知的病毒,谁会以一个肯定句去做解释?如果是,那么他肯定是个傻子。很显然高福主任不是一个傻子!希望大家能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中,有所甄别,有所取舍。
4.朋友圈得知“人传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猪一般的论调!
一点感触
传染病在社会公众认知中是片禁区,大家都觉得现代社会了哪还有什么传染病。其实不然,在此次疫情爆发之前,中疾控领导的预防控制体系消灭了多少次传染病危机,比如内蒙古鼠疫,本地登革热等。普通大众又知道多少呢?有媒体报道吗?ZF会通报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不让大众知晓呢?其实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正是预防控制体系默默的在背后保护着大众,甘愿做无名英雄,才有大家平安稳定的生活。但和平稳定的社会生活也导致了预防控制体系在各级 *** 都不受重视,收入待遇惨淡,比起临床医生那简直是天然之别,这更加速了预防控制体系人才流失,体系建设停滞。一旦遇到重大疫情,人才后劲不足,难以稳住局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我看来,作为此次舆论漩涡中的中疾控,乃至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是委屈无耐的。有功无人知,无错万人喷!
希冀
2月14日高瞻远瞩的提出15个体系9种机制4项制度,相信在这样强有力的文件的指导下,即使面对将来错综复杂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我国的疫情防控体系足以完美应对。预防体系建设是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核心,改革成败与否事关国民生计,预防控制系统建设胜,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胜!
以下为翻译后的论文
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早期传播动力学研究
Qun Li, M.Med., Xuhua Guan, Ph.D., Peng Wu, Ph.D., Xiaoye Wang, M.P.H., Lei Zhou, M.Med., Yeqing Tong, Ph.D., Ruiqi Ren, M.Med., Kathy S.M. Leung, Ph.D., Eric H.Y. Lau, Ph.D., Jessica Y. Wong, Ph.D., Xuesen Xing, Ph.D., Nijuan Xiang, M.Med., et al.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背景 在2019年12月和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感染肺炎(NCIP)的最早病例发生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我们分析了武汉市最初425例确诊病例的资料,以确定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 *** 我们收集了2020年1月22日之前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确诊病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接触史和疾病时间表。我们描述了病例的特点,并估计了关键的流行病学时延分布。在指数增长初期,我们估计了流行病倍增时间和基本繁殖数。结果 在前425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中,中位年龄59岁,56%为男性。在2020年1月1日前发病的病例中,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的占大多数(55%),而在随后的病例中,这一比例为8.6%。平均潜伏期为5.2天(95%置信区间为 4.1 ~ 7.0)。在早期阶段,感染人数每7.4天就扩大一倍。平均连续时间间隔为7.5天(95%置信区间为 5.3 ~ 19),基本繁殖数估计为2.2 (95%置信区间为 1.4 ~ 3.9)。结论 根据目前得到的基础信息,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了人传人。如果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将需要作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减少传播,以控制疫情。应在高危人群中实施预防或减少传播的措施。(由中国科学技术部等资助)
正文
自2019年12月以来,中国中部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感染肺炎(NCIP)病例。在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爆发后,全国建立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机制,故而当地医院使用这一监测机制进行上报,目的是及时识别新的病原体,如2019-nCoV。最近几天,中国其他城市和世界上十几个国家都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在此,我们通过对武汉市最初425例实验室确诊病例的数据进行分析,来描述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传播动力。
***
最早的病例是通过“不明原因肺炎”监测机制确定的。不明原因肺炎被定义为一种没有识别到特定病原体的疾病,且满足下列标准:发烧(≥38°C)、肺炎的影像学证据,白血球计数低或正常,淋巴细胞计数低,且标准临床抗菌治疗后3到5天没有改善。为了加强对肺炎病例的识别,并努力提高早期发现的敏感性,我们于2020年1月3日制定了一套量身定制的监测方案,用以识别潜在病例。一旦一个疑似病例被发现,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省、当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组成联合调查队伍,开始详细的实地调查和收集呼吸道标本,然后将标本送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检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小组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调查。
通过对感染者、亲属、密切接触者和医院医生的访谈,将数据收集到标准化表格中。我们收集了有关发病日期、就诊、住院和临床检验结果等相关信息。通过访谈和现场报告收集流行病学数据。调查采访每个感染患者和他们的亲戚,这是非常必要的,以确定患者疾病发病前两周期间的接触历史,包括接触任何野生动物的日期、时间、频率、和模式。还包括与其他有类似症状的人接触的信息。在实地调查期间收集的所有流行病学信息,包括接触史、事件时间线和密切接触者的识别,都与来自多个来源的信息进行了交叉核对。还调查了患者发病前2周内曾去过的家庭和地方,以评估可能的动物和环境暴露。数据输入中央数据库,一式两份,使用EpiData软件(EpiData Association)进行验证。
病例定义
最初疑似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定义是基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在2003年和2012推荐的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的病例定义。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发烧,肺炎的影像学证据,白细胞计数低或正常,淋巴细胞计数低,3天标准指南的抗菌治疗后,症状没有减轻。或者定义为满足上述前三个标准,并且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流行病学联系,或与其他有类似症状的患者有接触。,一旦获得关于确诊病例的新信息,我们会及时更新病例定义。总结标准如下:确诊病例-----在发病前14天内曾到武汉旅行或与来自武汉的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有直接接触,且呼吸道标本阳性。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检验至少以下三种 *** 之一:分离出2019 - ncov病毒,至少两次核酸检验阳性,测定样本基因序列2019 - ncov相匹配。
实验室检验
2019-nCoV实验室检测分析是基于世卫组织先前的建议。取患者上、下呼吸道标本。提取RNA,使用2019- ncov特异性引物和探针进行实时RT-PCR检测。试验分别在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病毒所的二级生物安全设施中进行。如果两个靶点(1a或1b,核衣壳蛋白)经特异性实时RT-PCR检测呈阳性,则视为实验室确诊。CT值小于37的循环阈值定义为阳性,大于40的循环阈值定义为阴性。如果ct值为37到40,需要通过重新测试进行确认。如果重复的ct值小于40且有明显的峰值,或者重复的ct值小于37,则认为复测为阳性。通过三种 *** 之一:桑格测序法、Illumina测序法或纳米孔测序法,从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样本中鉴定基因组。呼吸道标本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加强生物安全实验室3号设施的细胞中进行病毒分离。
统计分析
根据发病日期构建流行曲线,并叠加与疫情识别和控制措施相关的关键日期以辅助解释。描述了病例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接触和卫生保健工作者状况。潜伏期的分布(即通过拟合暴露史和发病日期数据的对数正态分布,并结合可获得的详细信息,估计了从感染到发病的时间延迟)。通过将威布尔分布与发病日期、首次就诊日期和住院日期在一个有详细信息的病例子集中进行拟合,来估计首次就诊日期和入院日期的分布。我们对来自群集调查的数据拟合了一个伽马分布来估计序列间隔分布,其定义为连续病例中疾病开始日期之间的延迟。
我们通过分析12月10日至1月4日期间发病病例的数据来估计疫情的增长率,因为我们预计在12月31日武汉正式宣布疫情爆发后不久,确诊的感染比例将会增加。我们模拟了传播模型(制定使用更新方程),我们使用这个模型来推导出流行的增长率,疫情倍增时间、数量和基本生殖(R0),它被定义为一个病例在感染周期内能感染几个健康人。我们使用了一个基于SARS序列区间的信息先验分布,其均值为8.4,标准差为3.8。
利用MATLAB软件(MathWorks)对潜伏期、序列间隔、生长速度和R0进行分析。其他分析使用SAS软件(SAS研究所)和R软件(R统计计算基金会)进行。
伦理审核
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委员会确定为流行性公共卫生疫情调查的一部分,因此被认为不需要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结果
疫情的发展遵循病例数的指数增长,最近几天的下降很可能是由于对最近发病和迟发的病例查明不足,而不是发病的真正转折点。具体地说,曲线的后一部分并不表示事件案件数量的减少,而是由于在截止日期确定案件的延误。在解释1月份病例的增长速度时应该谨慎,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测试包的可用性和使用都有所增加。大多数最早的病例据报暴露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但从12月下旬开始,非相关病例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患者的中位年龄为59岁(范围为15 - 89岁),425例患者中有240例(56%)为男性。15岁以下儿童无感染病例。我们调查了三个时间段的病例特征:之一个时间段是发病时间在1月1日之前,这是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闭的日期;第二阶段为1月1日至1月11日发病,当日为向武汉提供RT-PCR试剂;第三期为1月12日及以后发病(表1)。发病较早的患者年龄偏小,多为男性,多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出现。在这三个时期,卫生保健工作者中病例的比例逐渐增加(表1)。
我们检查了10例确诊病例的暴露数据,我们估计平均潜伏期为5.2天(95%置信区间
在截至2020年1月4日的疫情曲线上,日疫情增长率为0.10 (95% CI, 0.050 ~ 0.16),翻倍时间为7.4天(95% CI, 4.2 到14)。使用上面的连续区间分布,我们估计R0为2.2 (95% CI, 1.4到3.9)。
1月1日前45名患者从发病到就医平均估计5.8天(95% CI, 4.3 - 7.5),这类似于1月1日至1月11日之间207名患者发病到就医时间为平均4.6天(95% CI, 4.1 - 5.1)(图2)。44例1月1日前发病的患者从发病到住院的平均时间估计为12.5天(95%可信区间,10.3至14.8),比1月1日至11日发病的189例(平均9.1天)长(95% CI, 8.6到9.7)(图2D)。我们没有为1月12日或之后发病的患者绘制这些分布,因为那些近期发病和较长发病时间的患者尚未被检测到。
讨论
在此,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动力学和流行病学特征进行了初步评估。虽然大多数最早的病例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而且这些患者可能是通过人畜共患病或环境接触感染的,但现在清楚的是,已经发生了人传人,而且最近几周疫情已逐渐扩大。我们的发现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数,包括评价控制措施的影响和预测感染的未来传播。
我们估计R0约为2.2,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患者向2.2个其他人传播了感染。一般而言,只要R0大于1,疫情就会增加,控制措施的目的是将繁殖数量减少到1以下。SARS的R0估计在3左右,通过隔离病人和仔细的感染控制成功地控制了SARS的爆发。就新型冠状病毒而言,控制的挑战包括许多轻度感染的明显存在,以及隔离病例和隔离其密切接触者的有限资源。我们对R0的估计仅限于1月4日这段时间,因为对疫情认识的增强以及最近几周更多的可用性的检测手段的使用将增加确诊感染病例的比例。现在估计有可能在武汉的后续控制措施,以及最近在全国以及海外其他地方的控制措施,减少了传播性,但在国内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病例的检出表明疫情继续增强。虽然自1月23日起,武汉及其邻近城市的人口检疫应会减少向全国其他地区和海外的病例输出,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在其他地方是否也发生了类似强度的本地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病例很少发生在儿童中,425例中几乎有一半发生在60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中。儿童受感染的可能性可能较低,如果受感染,症状可能较轻。虽然在卫生保健工作者中发现了感染病例,但这一比例并不像SARS和MERS疫情期间那么高。SARS和MERS疫情的特征之一是传播能力的异质性,特别是在医院发生的超级传播事件。目前还没有确定新冠的超级传播事件,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它们可能成为一个可能。
我们对潜伏期分布的初步估计为对接触者实施14天医学观察期或检疫提供了重要证据。我们的估计是根据10个案件的资料作出的,有些不精确;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关这一分布的更多资料将是重要的。当获得更多关于新冠流行病学特征的数据时,与SARS和MERS的相应特征以及人类特有的四种冠状病毒的详细比较将是有益的。
我们的研究受到一种新出现的病原体感染的初步调查的诊断限制,特别是在最初阶段,当时对暴发的任何方面都知之甚少,并且缺乏诊断试剂。为了提高早期发现和诊断的敏感性,在病例鉴定中考虑了流行病学历史,并在获得更多信息后不断修改。1月11日在武汉提供PCR诊断试剂后,确诊病例更容易被发现,这帮助我们缩短了确诊时间。此外,最初的病例检测重点是肺炎患者,但我们现在了解到,一些患者可能出现胃肠道症状,也有儿童无症状感染的报道。早期非典型性感染可能被遗漏,在确诊病例中,临床感染程度可能未得到充分确定。我们没有关于疾病严重程度的详细信息来纳入这项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目前武汉地区新冠病例每7.4天左右就翻一番。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传人自12月中旬以来发生,并在此后一个月内逐渐传播。下一步措施包括确定最有效的控制措施,以减少社区内的传播。随着对流行病学特征和疫情动态了解的加深,病例定义可能需要进一步细化。应继续监测病例的特征,以确定流行病学方面的任何变化,例如,较年轻年龄组或卫生保健工作者中感染病例的增加。未来的研究可能包括对流行动态的预测和对家庭或其他地点的人传人的特别研究,以及确定亚临床感染发生率的血清监测将是有价值的。这些初步推断已列入“推论清单”,其中包括每个确诊病例的详细个人信息,但可能随着太多病例的出现而无法维持这种监测 *** ,可能需要其他 *** 替代。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应:转移病房不能算“已出现超级传播者”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记者王秉阳、屈婷)针对有媒体报道“已出现超级传播者”的说法,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应称:发生在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1名患者传染14名医务人员”事件,不能算“已出现超级传播者”。
记者了解到,25日有报道提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一名患者总共转了4次病房,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北京大学的一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位感染多位医务人员的患者可以被认定为‘超级传播者’。”
高福表示,由于该患者多次转移病房,所以不能算是“超级传播者”。“所以在卫生应急状态下,大家不要慌,优秀到位的管理非常重要。”
记者求证其他多位权威疾控专家,均认同高福对此的判断。
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说,还没有证据说已经有了“超级传播者”。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们当务之急是以科学思维开展防控治。”高福表示。